時(shí)時(shí)彩app官方下載 因上春晚他竟被封殺!這個(gè)為中國(guó)囊中靦腆的男東談主是時(shí)候說(shuō)了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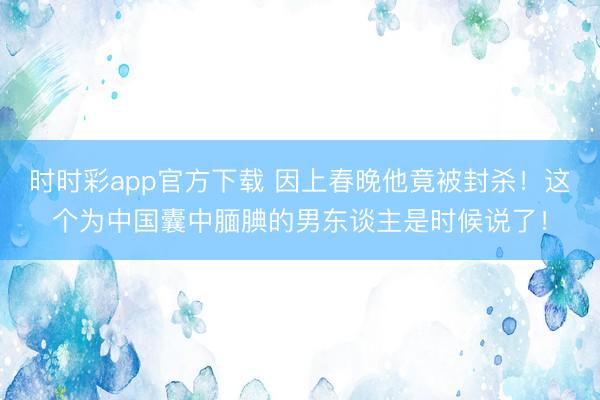
1984年春晚,一個(gè)身穿灰色中山裝的男東談主走上舞臺(tái),唱了一首歌。他一張口,電視機(jī)前,無(wú)數(shù)中國(guó)東談主霎時(shí)淚流滿面。
那晚事后,這首歌響徹了大江南北,他的名字——張明敏,也被億萬(wàn)國(guó)東談主記取。
但委果沒(méi)東談主知談,當(dāng)舞臺(tái)的燈光滅火,他回到香港的家,恭候他的不是榮耀,而是一場(chǎng)長(zhǎng)達(dá)14年的冰冷封殺。更沒(méi)東談主意料,幾年后,他會(huì)為了一件事,賣掉屋子和車子,湊出60萬(wàn),全部捐給國(guó)度。
他說(shuō):“我從不后悔。”
今天,我們就來(lái)聊聊這位歌手,和他那顆滾熱的“中國(guó)心”。
一、春晚前夕:一首無(wú)東談主敢要的“禁歌”
1982年的香港樂(lè)壇,富貴喧囂。但有一首歌,像一塊燒紅的炭,在音樂(lè)東談主手里傳來(lái)傳去,卻沒(méi)東談主敢接。
這首歌就是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。寫它的東談主,是大名鼎鼎的“鬼才”黃霑。
黃霑筆下從不缺金曲,但這首歌很相等。它用最樸素的普通話寫成,字里行間全是對(duì)于遠(yuǎn)處“故國(guó)”的深千里想念。這在其時(shí)的香港,是個(gè)極其敏銳的話題。
伸開(kāi)剩余96%那時(shí)的香港還在港英政府統(tǒng)帥下,社會(huì)環(huán)境復(fù)雜。文娛圈里有個(gè)不成文的禮貌:莫談國(guó)是,尤其別提“愛(ài)國(guó)”。誰(shuí)碰了,誰(shuí)的勞動(dòng)生涯就可能到頭。
演員梁家輝就是個(gè)活生生的例子。他因?yàn)橐徊侩娪叭?nèi)地拍戲,自后在受獎(jiǎng)禮上緩和說(shuō)我方是中國(guó)東談主,截至回到香港,勞動(dòng)契機(jī)霎時(shí)揮發(fā),最慘的時(shí)候不得不去街邊擺地?cái)偠讲焐?jì)。連他這樣有影帝頭銜的都如斯,更何況一個(gè)歌手?
是以,黃霑找了一圈,從當(dāng)紅巨星到后勁新東談主,統(tǒng)共東談主看到歌詞都搖頭。事理很一致:“霑叔,歌是好歌,但我不成唱,我還要吃飯。”
這首歌眼看就要被埋沒(méi)。
就在這個(gè)時(shí)候,有東談主向黃霑提了一個(gè)名字:張明敏。
其時(shí)的張明敏,在星光熠熠的香港樂(lè)壇,只是個(gè)不起眼的小扮裝。他不是全職歌手,白晝?cè)谝患译娮颖韽S當(dāng)工東談主,晚上和周末才去過(guò)問(wèn)一些業(yè)余歌唱比賽。他最大的建樹(shù),是拿過(guò)“全港工東談主演唱賽”和“全港業(yè)余歌手大賽”的雙料冠軍。在專科東談主士眼里,他酌定算個(gè)“靚聲王”,但離“明星”還差得遠(yuǎn)。
黃霑抱著試一試的心態(tài),找到了張明敏。他把歌譜遞疇前,沒(méi)繞彎子,平直把利害相干擺在了桌面上:“這首歌,唱的是我們的中國(guó)心。但在當(dāng)今這個(gè)環(huán)境下唱,你以后在香港,可能就沒(méi)得混了,你想了了。”
張明敏接過(guò)薄薄的歌譜,垂頭看了起來(lái)。房間里很舒坦,唯獨(dú)紙張翻動(dòng)的幽微聲響。
“邦畿只在我夢(mèng)縈,故國(guó)已多年未親近……”
他輕輕念了出來(lái)。念著念著,這個(gè)從小在香港長(zhǎng)大的后生,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情感撞擊著胸口。那種情感很生分,卻又像埋在心底很深入。歌詞里寫的長(zhǎng)江、長(zhǎng)城、黃山、黃河,他都沒(méi)親眼見(jiàn)過(guò),但合計(jì)無(wú)比親切。
“洋裝天然穿在身,我心依然是中國(guó)心……”
就這一句,讓他鼻子一酸。是啊,盡管生活在香港,一稔西裝,說(shuō)著粵語(yǔ),可實(shí)踐里流著的血,奈何會(huì)變呢?
他委果莫得耽擱,抬動(dòng)手對(duì)黃霑說(shuō):“霑叔,這首歌,我唱。”
黃霑有點(diǎn)不測(cè),追問(wèn)談:“你不怕?”
張明敏回應(yīng):“沒(méi)什么好怕的。我只是唱出了心里話。”
很快,張明敏走進(jìn)了灌音棚。莫得豪華的樂(lè)隊(duì),莫得復(fù)雜的編曲,他用最真誠(chéng)、以致有些粗劣的普通話,錄收?qǐng)鲞@首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。錄制經(jīng)由很到手,因?yàn)榍殂菏谴_切,統(tǒng)共的手段在真情實(shí)感眼前,都顯得過(guò)剩。
唱片出來(lái)了,封面樸素。張明敏沒(méi)指望它能賣幾許,他只是完成了一樁心愿。
不出所料,這張唱片在香港市集委果沒(méi)激起任何水花。電臺(tái)不肯意播,唱片行把它放在最不起眼的邊際。更現(xiàn)實(shí)的打擊相繼而至:他簽約的唱片公司,因?yàn)橛浤钸@首歌帶來(lái)的“政事風(fēng)險(xiǎn)”,輕浮地和他鏟除了合約。
通宵之間,他從一個(gè)剛有點(diǎn)起色的業(yè)余歌手,釀成了休閑后生。音樂(lè)這條路,眼看就要被他我方“唱”斷了。
身邊的親戚一又友都勸他:“明敏,算了吧,認(rèn)清現(xiàn)實(shí)。找個(gè)踏實(shí)勞動(dòng),好好過(guò)日子,唱歌就當(dāng)個(gè)注意。”
張明敏沒(méi)話語(yǔ)。他摸著那張銷量慘淡的唱片,心里有失意,但莫得后悔。他只是微辭合計(jì),這首歌的勞動(dòng),似乎還莫得信得過(guò)啟動(dòng)。
二、北京來(lái)電:交運(yùn)般的春晚邀請(qǐng)函
技能走到1984年。這是一個(gè)對(duì)舉座中國(guó)東談主而言都意旨零星的年份。這一年,中英兩國(guó)政府認(rèn)真簽署了對(duì)于香港問(wèn)題的連結(jié)聲明,向全世界宣告:香港,將于1997年7月1日歸來(lái)中國(guó)。
這個(gè)音訊像春雷相同滾過(guò)神州地面,無(wú)數(shù)東談主為之豪邁歡喜。一種渴慕國(guó)度統(tǒng)一、民族聚積的強(qiáng)烈情感,在社會(huì)上富饒開(kāi)來(lái)。
在北京,中央電視臺(tái)的春晚劇組辦公室里,總導(dǎo)演黃一鶴正在為除夕夜的節(jié)目狼狽不堪。他想為這個(gè)零星的年份,作念點(diǎn)不相同的東西。
一天,他巧合從收音機(jī)里聽(tīng)到了一首歌,旋律昂然,歌詞直白卻充滿力量——“長(zhǎng)江,長(zhǎng)城,黃山,黃河,在我心中重千斤……”他猛地坐直了身段,豪邁地拍了下桌子:“就是它!就是這種嗅覺(jué)!”
他坐窩讓勞動(dòng)主談主員去查,這首歌是誰(shuí)唱的。很快,張明敏的名字和那卷灌音帶,擺在了他的案頭。
黃一鶴導(dǎo)演心里萌發(fā)了一個(gè)斗膽到有些冒險(xiǎn)的想法:邀請(qǐng)這位香港歌手,登上春晚的舞臺(tái),現(xiàn)場(chǎng)演唱這首歌。
這個(gè)想法一建議,劇組里面就炸開(kāi)了鍋。
反對(duì)的辦法很現(xiàn)實(shí):“導(dǎo)演,這風(fēng)險(xiǎn)太大了!他是個(gè)香港歌手,布景我們完全不了解。讓他上春晚,照舊唱這樣一首歌,萬(wàn)一出點(diǎn)政事問(wèn)題,誰(shuí)能擔(dān)得起這個(gè)背負(fù)?”
“是啊,況且他的普通話……聽(tīng)著也不太圭臬。在寰宇東談主民眼前,能行嗎?”
{jz:field.toptypename/}黃一鶴據(jù)理力求,他的事理很簡(jiǎn)略,卻很有勁:“你們聽(tīng),他唱得不圭臬,但情愫是百分之百確切!我們當(dāng)今需要的,就是這種真情愫。香港要回來(lái)了,我們需要一個(gè)聲氣,告訴寰宇東談主民,也告訴全世界,香港同族和我們心連著心!我看張明敏,就是最符合的東談主選。”
幾經(jīng)險(xiǎn)阻,邀請(qǐng)函高出大大小小,從北京寄到了香港張明敏的手中。
當(dāng)張明敏終止那封來(lái)自“中央電視臺(tái)”的信件時(shí),手都有些發(fā)抖。他反復(fù)讀了好幾遍,才闡發(fā)這不是作念夢(mèng)——中國(guó)最高規(guī)格的文藝晚會(huì),邀請(qǐng)他去扮演,唱的恰是那首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。
巨大的喜悅霎時(shí)覆沒(méi)了他。但緊接著,深深的憂慮爬上了心頭。
他太了了接下這個(gè)邀請(qǐng)意味著什么了。在香港,唱國(guó)語(yǔ)愛(ài)國(guó)歌曲也曾是“異類”,若是再去內(nèi)地的最高舞臺(tái)演唱,那委果等于公開(kāi)“站隊(duì)”。等他回來(lái),恐怕就不是苛待那么簡(jiǎn)略了,很可能被透頂封殺,在香港文娛圈再無(wú)一席之地。
一又友們知談后,都趕來(lái)勸他。
“明敏,你瘋啦?你知談去了之后回來(lái)會(huì)如何嗎?你的奇跡就全收?qǐng)觯 ?/p>
“你當(dāng)今天然不紅,但至少還能在酒吧唱唱歌,接點(diǎn)小行為。去了春晚,你連這些都沒(méi)了!”
“三想啊,那但是你的出路!”
那通宵,張明敏失眠了。他躺在床上,盯著天花板,腦海里兩個(gè)聲氣在猛烈爭(zhēng)吵。一個(gè)聲氣說(shuō):“這是千載難逢的契機(jī),你的歌能被億萬(wàn)同族聽(tīng)到,這是歌手的至高榮耀!”另一個(gè)聲氣說(shuō):“別犯傻,你在香港長(zhǎng)大,你的生活、奇跡、一又友都在這里,毀了這一切,值得嗎?”
他爬起來(lái),又聽(tīng)了一遍我方錄的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。當(dāng)“不管何時(shí),不管何地,心中相同親”的旋律響起時(shí),他作念出了決定。
天快亮?xí)r,他給北京回了電話,只說(shuō)了簡(jiǎn)短的幾個(gè)字:“謝謝邀請(qǐng),我一定到。”
放下電話,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削弱。遠(yuǎn)景未卜,但心卻定了。
三、通宵之間:從“無(wú)名小卒”到“全民偶像”
1984年農(nóng)歷除夕,中央電視臺(tái)演播大廳。燈光、錄像機(jī)、現(xiàn)場(chǎng)不雅眾的眼神,一切都準(zhǔn)備就緒,空氣中富饒著病篤而興盛的氣味。
張明敏站在后臺(tái)候場(chǎng),手心全是汗。他一稔有利定作念的一身灰色中山裝,挺拔,莊重。這是他第一次來(lái)到北京,第一次踏上這樣大的舞臺(tái),第一次面臨數(shù)億不雅眾。他反復(fù)默念著歌詞,或許出一丁點(diǎn)差錯(cuò)。
主理東談主報(bào)出了他的名字和曲目。他深吸連續(xù),邁著妥貼的次第,走向舞臺(tái)中央。聚光燈“啪”地打在他身上,有些奪目。他能看到臺(tái)下黑壓壓的不雅眾,能聽(tīng)到我方腹黑“砰砰”狂跳的聲氣。
前奏響起,老練而謹(jǐn)慎。他舉起發(fā)話器,閉上眼睛,遠(yuǎn)隔了統(tǒng)共的病篤和雜念,再睜開(kāi)時(shí),眼里只剩下一派誠(chéng)篤。
“邦畿只在我夢(mèng)縈,故國(guó)已多年未親近……”
他的嗓音甘醇,帶著赫然的粵語(yǔ)口音,吐字算不上南腔北調(diào),但每一句都仿佛用盡了全身的力氣,從心底最深處掏出來(lái)。莫得炫技,莫得夸張的肢體動(dòng)作,他就那樣平直地站著,用最真誠(chéng)的方式,傾吐著。
臺(tái)下,起始是舒坦的。逐漸地,有不雅眾啟動(dòng)隨著旋律輕輕點(diǎn)頭。當(dāng)唱到“長(zhǎng)江,長(zhǎng)城,黃山,黃河,在我心中重千斤”時(shí),許多東談主的眼眶也曾啟動(dòng)濕潤(rùn)。
“不管何時(shí),不管何地,心中相同親……”
電視機(jī)前,這幅景象在千門萬(wàn)戶同步上演。除夕飯的餐桌旁,東談主們放下了筷子;正在玩鬧的孩子,被父母叫到身邊;勤勉的主婦,停駐了手中的活計(jì)。無(wú)數(shù)的家庭,在這一刻,被團(tuán)結(jié)首歌擊中。
一位閱歷過(guò)戰(zhàn)亂的老華裔,聽(tīng)到這里,淚流滿面,對(duì)著電視里的張明敏不住點(diǎn)頭。一個(gè)朔方的工東談主家庭,父親指著電視對(duì)男兒說(shuō):“聽(tīng)見(jiàn)沒(méi),這就是我們的根。”南邊的校園里,寢室樓傳出了跟唱的聲氣,起始是一兩個(gè),自后釀成一派。
三分多鐘的演唱,很快竣事了。臨了一個(gè)音符落下,演播大廳出現(xiàn)了幾秒鐘的絕對(duì)寂寥。緊接著,雷鳴般的掌聲轟然爆發(fā),持續(xù)了快要一分鐘。臺(tái)下許多不雅眾,一邊用勁飽讀掌,一邊擦著眼淚。
張明敏向著不雅眾,深深地、圭臬地鞠了一躬。抬動(dòng)手時(shí),他的眼圈也紅了。他知談,他唱出來(lái)了,億萬(wàn)同族,都聽(tīng)到了。
那一晚,中國(guó)出身了一個(gè)前所未有的“景象級(jí)”傳播事件。在阿誰(shuí)通信不領(lǐng)悟的年代,張明敏和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以衣缽相傳的速率,火遍寰宇。三街六巷,男女老幼,委果東談主東談主都會(huì)哼上兩句“流在心里的血,滂沱著中華的聲氣”。
張明敏這個(gè)名字,開(kāi)云體育app從一個(gè)香港的業(yè)余歌手,一躍成為十億中國(guó)東談主心中的“愛(ài)國(guó)歌手”代表。多樣上演邀請(qǐng)、采訪懇求,從故國(guó)的四面八方雪片般飛來(lái)。
他東談主生中第一次,體會(huì)到了什么是“頂流”的滋味。走在內(nèi)地的街上,會(huì)被東談主認(rèn)出來(lái),要求簽名合影;報(bào)紙上,他的名字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;播送里,全天候播放著他的歌。他勤勉而興盛地穿梭于各個(gè)城市之間,享受著這份出乎意料的、巨大的榮耀。
關(guān)聯(lián)詞,在這片悶熱的“暖流”之中,唯獨(dú)他我方知談,心底有一塊場(chǎng)地,永久是冰涼而緊繃的。他了了,當(dāng)他在內(nèi)地享受鮮花和掌聲時(shí),在香港,一場(chǎng)針對(duì)他的“寒流”正在急劇集聚、醞釀。
春晚的爽快,像一場(chǎng)璀璨卻局促的夢(mèng)。夢(mèng),老是要醒的。
四、冰封香江:那長(zhǎng)達(dá)十四年的“隱匿”
竣事了在內(nèi)地的轟動(dòng)性巡演,張明敏拖著苦楚卻興盛的身段,回到了香港。
機(jī)場(chǎng)的歧視有些異樣。莫得記者,莫得歌迷,老練的香港媒體仿佛集體失明,對(duì)他這個(gè)“載譽(yù)歸來(lái)”的歌手目大不睹。他拉著行李走出閘口,心里那根繃緊的弦,“咯噔”響了一下。
信得過(guò)的涼爽,從第二天啟動(dòng)全面襲來(lái)。
先是唱片公司打來(lái)認(rèn)真電話,口吻冰冷地見(jiàn)告他,統(tǒng)共協(xié)作即刻終止,此前刊行的唱片全手下架、點(diǎn)燃。事理很官方,也很焦慮:“市集反響欠安,且藝東談主形象與公司發(fā)展商量不符。”
接著,是買賣上演的全面凍結(jié)。以往那些偶爾還會(huì)邀請(qǐng)他去暖場(chǎng)的酒吧、買賣行為,如今王人備關(guān)上了大門。電話打疇前,對(duì)方不是支茍且吾,就是平直掛斷。以致有行為主辦方直言:“張先生,不是你的歌不好,是我們不敢用你。用了你,我們其他的藝東談主可能也會(huì)受遭災(zāi)。”
最讓他感到透骨的,是來(lái)自同業(yè)和部分媒體的魄力。在一些公開(kāi)場(chǎng)合,熟東談主見(jiàn)到他,會(huì)刻意遁藏眼神,或者繞談而行。一些小報(bào)啟動(dòng)刊登含沙射影的著述,嘲諷他是“投契分子”,為了恭維內(nèi)地不吝殉難土產(chǎn)貨出息。更有甚者,給他扣上了莫須有的“政事帽子”。
委果是通宵之間,張明敏在香港樂(lè)壇“被隱匿”了。電臺(tái)里再也聽(tīng)不到他的歌,電視上看不到他的影,報(bào)紙文娛版也莫得他的音訊。他就好像一顆也曾濺起過(guò)些許水花的小石子,透頂千里入了深不見(jiàn)底的水潭。
生活一下子從璀璨的云表,跌回了冰冷的現(xiàn)實(shí)。莫得了收入,積蓄很快見(jiàn)底。最艱巨的時(shí)候,他連房租都成問(wèn)題。為了生涯,他不得不放下“歌手”的身段,去嘗試多樣零工。他幫東談主送過(guò)貨,在一又友的店鋪里打過(guò)雜,以致想過(guò)要不要重來(lái)電子表廠。
比經(jīng)濟(jì)拮據(jù)更折磨東談主的,是精神上的孤苦與迷濛。夜深,他不時(shí)失眠,望著香港妍麗的夜景,內(nèi)心一派凄滄。他啟動(dòng)懷疑我方當(dāng)初的羅致:為了唱那一首歌,為了那一次登臺(tái),賭上我方統(tǒng)共這個(gè)詞的奇跡和生活,確切值得嗎?若是當(dāng)初拒卻了春晚的邀請(qǐng),當(dāng)今會(huì)不會(huì)是另一番光景?
每當(dāng)這種自我懷疑升空時(shí),他就會(huì)走到窗邊,小聲地、反復(fù)地哼唱那首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。唱著唱著,那股熱血又會(huì)徐徐涌回胸膛。
“沒(méi)錯(cuò),我不后悔。”他對(duì)我方說(shuō),“我唱的是我的忠誠(chéng),這份忠誠(chéng),莫得錯(cuò)。”
就在他東談主生最低谷、最昏黑的時(shí)期,來(lái)自內(nèi)地的信件,成了照進(jìn)他生命罅隙里的光。這些信,來(lái)自日東月西,有的筆跡精巧,有的歪七扭八。寫信的東談主,有工東談主、農(nóng)民、學(xué)生、教悔……
“張明敏先生,我們?nèi)叶伎蓯?ài)你的歌,你的《中國(guó)心》唱到我們心坎里了。你要對(duì)峙住!”
“我們搭救你!你是信得過(guò)的中國(guó)東談主!”
“但愿能再聽(tīng)到你唱歌,來(lái)我們這里吧,我們給你搭臺(tái)子!”
這些樸素真摯的話語(yǔ),給了張明敏莫大的溫順和力量。他雄厚到,我方并非孤身一東談主。在遠(yuǎn)處的朔方,罕有以億計(jì)的同族在搭救他、記起他。
恰在此時(shí),一些內(nèi)地的上演機(jī)構(gòu),也頂著某種壓力,向他發(fā)出了針織的邀請(qǐng)。他們但愿他能到內(nèi)地來(lái),為老匹夫唱歌。
去,照舊不去?
在香港,他已楚囚對(duì)泣。去內(nèi)地,意味著他將透頂坐實(shí)某些“標(biāo)簽”,大致再無(wú)回頭之路。但那里,有恭候他的舞臺(tái),有渴慕他歌聲的不雅眾,有能讓他接續(xù)當(dāng)作又名歌手生涯下去的空間。
委果莫得太多抗?fàn)帲瑥埫髅糇髂畛隽藳Q定:北上。
他打理了簡(jiǎn)略的行囊,告別了白眼與荒僻的香港,再次踏上了趕赴內(nèi)地的路程。這一次,他的心境與春晚時(shí)截然有異,少了幾分興盛與榮耀感,多了幾分激越與決絕。他不知談前路如何,但他知談,他必須唱下去,為了那些記起他的東談主,也為了我方那顆未始滅火的“中國(guó)心”。
五、情義無(wú)價(jià):154場(chǎng)義演與60萬(wàn)毛票
上世紀(jì)80年代末的中國(guó),正處在讎校綻放的興盛與躁動(dòng)中,全社會(huì)都憋著一股勁,想向世界解釋我方。1990年,北京亞運(yùn)會(huì),就是這樣一個(gè)歷史性的機(jī)遇。這是中國(guó)第一次經(jīng)辦大型海外詳細(xì)認(rèn)知會(huì),意旨超卓。
關(guān)聯(lián)詞,舉辦如斯范圍的嘉會(huì),需要廣大資金。其時(shí)國(guó)度財(cái)力有限,亞運(yùn)會(huì)的籌備勞動(dòng)遭遇了巨大的資金缺口。組委會(huì)向社會(huì)發(fā)出了“東談主東談主捐錢辦亞運(yùn)”的號(hào)召,但籌資進(jìn)展依然緩慢。
這個(gè)音訊,傳到了正在內(nèi)地沉重進(jìn)行巡回上演的張明敏耳中。他委果莫得任何耽擱,心里就蹦出一個(gè)念頭:我要為亞運(yùn)會(huì)作念點(diǎn)什么。
可奈何作念呢?他彼時(shí)在香港被封殺,在內(nèi)地的上演也多是小范圍、低報(bào)答的,個(gè)東談主積蓄在漫長(zhǎng)的“休閑”和北上馳驅(qū)中,早已所剩無(wú)幾。他唯一領(lǐng)有的,就是我方的歌聲,時(shí)時(shí)彩app和因?yàn)椤段业闹袊?guó)心》而積存的一絲知名度。
一個(gè)近乎狂放的主見(jiàn),在他腦海中成形:舉辦巡回義演,把統(tǒng)共收入,一分不剩,全部捐給亞運(yùn)會(huì)!
他把這個(gè)想法告訴了身邊僅有的幾個(gè)伙伴和一又友。環(huán)球都驚呆了。
“明敏,你緩和點(diǎn)!你當(dāng)今的處境,哪還有錢搞巡回上演?時(shí)局、樂(lè)隊(duì)、交通、住宿,哪相同不要錢?”
“就算上演,票價(jià)定高了沒(méi)東談主看,定低了,演一百場(chǎng)也湊不了幾個(gè)錢,你這是白辛苦!”
“況且,這完全是無(wú)償?shù)模阄曳降娜兆舆€過(guò)不外了?”
張明敏千里默了一會(huì)兒,然后緩和地說(shuō):“錢,我來(lái)想辦法。日子,總能過(guò)下去的。但亞運(yùn)會(huì),國(guó)度需要,我必須盡這份力。”
他回到了香港,作念出了一個(gè)讓統(tǒng)共東談主都難以置信的決定:賣掉我方唯一的房產(chǎn)和代步的汽車。 那是他多年辛苦攢下的一絲家當(dāng),是在香港容身立命的根底。
親戚一又友們聞?dòng)嵹s來(lái)規(guī)勸,母親更是哭著對(duì)他說(shuō):“孩子,你這是要把我方的后路都斷掉啊!沒(méi)了屋子,你以后住那兒?沒(méi)了車,你奈何跑生活?”
張明敏抓著母親的手,眼圈發(fā)紅,但口吻顛倒強(qiáng)項(xiàng):“媽,屋子車子沒(méi)了,以后還能掙。可國(guó)度辦亞運(yùn)會(huì),這是百年不遇的大事。我別的莫得,就會(huì)唱幾首歌,若是這時(shí)候我不作念點(diǎn)什么,我一輩子都會(huì)不釋懷。這些錢,就當(dāng)是我這個(gè)男兒,給故國(guó)母親盡的一絲孝心吧。”
屋子和車子賣了,湊出了一筆啟動(dòng)資金。帶著這筆錢,張明敏回到了內(nèi)地,締造了輕便的“張明敏為亞運(yùn)義演籌備組”。莫得專科的規(guī)劃團(tuán)隊(duì),莫得麗都的宣傳包裝,一切都因陋就簡(jiǎn)。
他的團(tuán)隊(duì)找到各地的工會(huì)、文化宮、體育館,用最樸素的語(yǔ)言相通:“我們想為亞運(yùn)會(huì)義演,門票收入全部捐獻(xiàn),票價(jià)就定幾毛錢,讓老匹夫都看得起。”
票價(jià)最終定在三毛、五毛、一塊三個(gè)層次。這在其時(shí),也不外是一根冰棍、一個(gè)面包的錢。好多東談主不睬解,合計(jì)這根底是在“亂彈琴”,靠這樣點(diǎn)錢,想湊出廣大捐錢,無(wú)異于癡東談主說(shuō)夢(mèng)。
張明敏不管這些。1988年頭,他的亞運(yùn)義演,從朔方的一座工業(yè)城市認(rèn)真啟動(dòng)了。
第一場(chǎng),在一個(gè)老舊的文化宮會(huì)堂。舞臺(tái)輕便,音響截至也很一般。但能容納一千多東談主的會(huì)堂,觀者云集,連過(guò)談都站滿了東談主。不雅眾們手里舉著小小的國(guó)旗,眼神緊迫。
當(dāng)張明敏走上臺(tái),莫得過(guò)多寒暄,平直唱起了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。臺(tái)下,從第一句啟動(dòng),就是千東談主大齊唱。唱到動(dòng)情處,好多東談主一邊唱,一邊流眼淚。那不是悼念的淚,是一種豪邁、一種共識(shí)、一種集體情感宣泄的淚。
一場(chǎng),兩場(chǎng),十場(chǎng),五十場(chǎng)……張明敏的義演之路,就這樣一場(chǎng)接一時(shí)局走了下去。他的行程表密密匝匝,不時(shí)一天要趕兩三個(gè)城市,上晝?cè)谶@個(gè)縣的戲院唱完,下晝就要坐幾個(gè)小時(shí)的資料車,趕到下一個(gè)市的體育館。
吃飯,就在路邊攤粗疏料理;睡眠,不時(shí)是在泛動(dòng)的車上或者低價(jià)的迎接所里對(duì)付。 高強(qiáng)度、連軸轉(zhuǎn)的上演,讓他的嗓子永恒處于充血景況,嘶啞成了常態(tài)。隨身必備的不是什么保健品,而是最低廉的潤(rùn)喉糖。
有一次,在南邊某市上演,突降暴雨。開(kāi)演前,體育館外電閃雷鳴,積水沒(méi)過(guò)腳踝。勞動(dòng)主談主員記念不雅眾來(lái)得少,建議推遲或者取消。張明敏看著窗外的大雨,搖搖頭:“定了的技能,就不成改。哪怕臺(tái)下唯惟一位不雅眾,我也要唱。”
截至,那天晚上,體育館里依然坐滿了撐著傘、披著雨衣前來(lái)的不雅眾。看著臺(tái)下那一張張雨水打濕卻眷注不減的臉,張明敏在臺(tái)上深深鞠躬,久久莫得起身。那一場(chǎng),他唱得格外賣力,仿佛要把統(tǒng)共的能量,都獻(xiàn)給這些可人的同族。
雷同的故事,在接下來(lái)的日子里連接上演。在西北,他頂著沙塵暴演唱;在礦區(qū),他深入到井口為工東談主們清唱;在學(xué)校,他飽讀動(dòng)孩子們要為國(guó)爭(zhēng)氣。
他的舞臺(tái),有時(shí)是正規(guī)的戲院,有時(shí)是學(xué)校的操場(chǎng),有時(shí)以致是田間地頭的臨時(shí)搭臺(tái)。要求沉重,但他從不否認(rèn)。每一場(chǎng),他都唱足重量,每一場(chǎng),他都會(huì)屬目地講起亞運(yùn)會(huì)的意旨,號(hào)令環(huán)球搭救國(guó)度。
他的真誠(chéng),打動(dòng)了無(wú)數(shù)普通東談主。好多不雅眾聽(tīng)完演唱會(huì),不僅買了票,還主動(dòng)把身上過(guò)剩的錢塞進(jìn)募捐箱。有老大娘掏起首絹,把里面包著的零錢全部倒了進(jìn)去;有小一又友砸碎我方的存錢罐,捧著一大把硬幣來(lái)捐錢;有經(jīng)濟(jì)要求好些的個(gè)體戶,平直留住幾十元、上百元,那是其時(shí)一個(gè)東談主好幾個(gè)月的工資。
錢,一筆一筆地匯攏;上演,一場(chǎng)一時(shí)局累積。
整整一年技能,張明敏的腳跡遍布大江南北,從最北的黑龍江,到最南的廣東,他跑遍了寰宇二十多個(gè)省、上百個(gè)市縣。最終的數(shù)字定格在:154場(chǎng)。
當(dāng)義演全部竣事,團(tuán)隊(duì)啟動(dòng)盤點(diǎn)捐錢。那是一個(gè)極其震撼的場(chǎng)面:成捆成捆的毛票、硬幣,堆滿了房間的幾個(gè)邊際。 最大面額是十元,更多的是五元、兩元、一元,以及多量的五毛、兩毛、一毛紙幣和硬幣。
勞動(dòng)主談主員和銀行職員一談,花了整整幾天技能,才把這些沾染著汗?jié)n、帶著不同場(chǎng)地泥村炮味的零錢盤點(diǎn)完畢。最終的數(shù)字是:60萬(wàn)元東談主民幣。
在80年代末,這無(wú)疑是一筆巨款。它不僅是錢,更是154個(gè)晝夜的馳驅(qū),是數(shù)百萬(wàn)東談主次的誠(chéng)篤之心,是一個(gè)歌手傾其統(tǒng)共、掏心掏肺的愛(ài)國(guó)之舉。
張明敏躬行把這60萬(wàn)元,送到了北京亞運(yùn)會(huì)籌資委員會(huì)。他莫得舉行任何慶典,莫得見(jiàn)告任何媒體,就像完成一件必須完成的隱痛,暗暗地來(lái),又暗暗地離開(kāi)。
錢捐出去了,亞運(yùn)會(huì)的場(chǎng)館一棟棟建了起來(lái)。張明敏的身段也委果垮了,永恒的勞累和養(yǎng)分不良,讓他瘦了十幾斤,嗓音也變得不如從前清澈。
他回到了香港,依舊面臨阿誰(shuí)冷颼颼的、封殺他的世界。賣掉的屋子莫得了,他租住在微細(xì)的舊屋里;車子莫得了,他外出就擠巴士、地鐵。生活,似乎又回到了原點(diǎn),以致比原點(diǎn)更沉重。
但每當(dāng)夜深東談主靜,苦楚不勝時(shí),他想起那154個(gè)鼎沸的夜晚,想起臺(tái)下那些含淚齊唱的面目,想起那堆積如山的零錢,心里就會(huì)涌起一股暖流和力量。
他作念了他認(rèn)為對(duì)的事,這就夠了。至于疇昔的路,走下去即是。
六、千里默的信守:在“被淡忘”的歲月里
亞運(yùn)會(huì)義演之后,張明敏在內(nèi)地的名聲達(dá)到了一個(gè)新的高度。他被譽(yù)為“愛(ài)國(guó)歌手”的典范,功績(jī)被平時(shí)報(bào)談。關(guān)聯(lián)詞,這些榮光,依舊無(wú)法穿透那談橫亙?cè)诹_湖橋南側(cè)的無(wú)形樊籬。
回到香港,他面臨的依然是阿誰(shuí)老練的、冰冷的文娛圈。封殺令莫得因?yàn)樗趦?nèi)地的善舉而有涓滴松動(dòng)。電臺(tái)的播放列內(nèi)外莫得他,電視的文娛節(jié)目里莫得他,報(bào)紙的八卦版面也懶得再提他。他仿佛成了香港文娛史上一個(gè)被刻意抹去的名字。
最現(xiàn)實(shí)的問(wèn)題是生涯。義演所得全部捐獻(xiàn),他再次變得賜墻及肩。唱歌這條路,在香港也曾被透頂堵死。他必須尋找新的活法。
中年轉(zhuǎn)行,談何容易。他嘗試過(guò)好多勞動(dòng)。和幾個(gè)一又友聯(lián)合開(kāi)過(guò)服裝店,從跑面料市集、盯成衣加工到站柜臺(tái)銷售,事事親力親為。但隔行如隔山,對(duì)市集判斷的紕謬和規(guī)劃不善,店鋪沒(méi)撐持多久就關(guān)門了,還欠下了一些債務(wù)。
自后,他又嘗試開(kāi)了一家小餐館。他放下也曾在舞臺(tái)上的身段,系上圍裙,從采購(gòu)、洗菜、呼叫賓客作念起。小店滋味可以,價(jià)錢也實(shí)惠,起始生意尚可。但香港餐飲業(yè)競(jìng)爭(zhēng)猛烈,加上他名東談主身份帶來(lái)的玄機(jī)影響——有些顧主是出于敬愛(ài)而來(lái),有些則可能刻意遁藏——小餐館的生意亦然起起落落,最終難以為繼。
那幾年,是他東談主生中最低調(diào)、最千里寂,也最艱辛的歲月。他不再是舞臺(tái)上阿誰(shuí)后光四射的歌手,而是一個(gè)為生老病死發(fā)愁的普通中年男東談主。也曾協(xié)作過(guò)的音樂(lè)東談主,大多已功成名就;樂(lè)壇新東談主輩出,再?zèng)]東談主拿起“張明敏”三個(gè)字。巨大的落差感,技能啃噬著他的內(nèi)心。
唯一不變的,是他家里那臺(tái)舊式灌音機(jī),和那盤反復(fù)播放、邊緣都已磨損的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磁帶。在無(wú)數(shù)個(gè)苦楚歸來(lái)的夜晚,在生意失敗后的黯然技能,他都會(huì)按下播放鍵。歌聲響起,仿佛能帶他穿越回阿誰(shuí)掌聲雷動(dòng)的春晚舞臺(tái),回到那些萬(wàn)東談主齊唱的義演現(xiàn)場(chǎng)。
音樂(lè),是他臨了的慰藉,亦然撐持他走下去的信念。他投降,我方羅致的談路莫得錯(cuò),愛(ài)我方的國(guó)度,是稟賦東談主權(quán),是理所天然。他只是在舛錯(cuò)的技能、舛錯(cuò)的地點(diǎn),作念了正確的事。
內(nèi)地來(lái)的信,依舊隔三差五地寄到他的故我址。這些信,成了他與過(guò)往榮耀、與那片繁多地皮之間最溫順的有關(guān)。一些內(nèi)地的上演邀請(qǐng),也依然會(huì)迂回找到他。只須要求允許,他依然會(huì)閑適趕赴。在那里,他還能找到歌手的價(jià)值,還能感受到被需要、被尊重的溫順。
技能,在千里默和信守中緩緩流淌。日期一頁(yè)頁(yè)翻過(guò),從80年代翻到90年代。香港歸來(lái)的日期,越來(lái)越近。社會(huì)的氛圍,也在悄無(wú)聲氣地發(fā)生著變化。
張明敏是非地嗅覺(jué)到,那股秘密在他頭頂?shù)暮猓坪踉谛煨鞙p退。一些老一又友啟動(dòng)從頭有關(guān)他,言語(yǔ)中多了幾分唏噓和調(diào)處;小數(shù)數(shù)袖珍的、非主流的社區(qū)行為,也啟動(dòng)試探性地邀請(qǐng)他去唱一兩首歌。天然主流媒體的大門依然阻塞,但罅隙中的微光,也曾蒙朧可見(jiàn)。
他像一塊被深埋地下的璞玉,在漫長(zhǎng)的昏黑和壓力中,肅靜恭候著破土重出的那一天。他莫得高聲快什么,莫得怨天尤東談主,只是舒坦地生活,勤苦地勞動(dòng),呆板地守護(hù)著我方那顆從未改造的“中國(guó)心”。
他知談,歷史的大潮,正在不可逆轉(zhuǎn)地朝著一個(gè)標(biāo)的奔涌。而他個(gè)東談主的交運(yùn),也終將與這股大潮淡雅連結(jié)。他所需要作念的,只是恭候,并投降。
七、歸來(lái):那一聲“故國(guó)莫得健無(wú)私”
1997年,終于來(lái)了。
這一年的7月1日,全世界的眼神都聚焦在香港。零時(shí)整,跟隨著雄渾的中華東談主民共和國(guó)國(guó)歌,五星紅旗和紫荊花區(qū)旗在香港會(huì)展中心徐徐升空。中國(guó)政府規(guī)復(fù)對(duì)香港哄騙主權(quán)。
那一刻,坐在電視機(jī)前的張明敏,淚水奪眶而出。為了這一天,中國(guó)東談主等了太久,他個(gè)東談主,也等了太久。百余年殖民歷史的閉幕,意味著一個(gè)新時(shí)期的開(kāi)啟,也意味著,壓在他身上那副無(wú)形的鐐銬,終于到了該解開(kāi)的時(shí)候。
歸來(lái)之后,香港的社會(huì)氛圍發(fā)生了根人道的升沉。愛(ài)國(guó)愛(ài)港,成為社會(huì)主流價(jià)值不雅。那些也曾被視為“敏銳”以致“禁忌”的話題和行徑,如今成了光榮和自負(fù)。
委果是在歸來(lái)后的第一技能,香港和內(nèi)地的多樣官方、民間文化交流行為便昌盛開(kāi)展起來(lái)。而張明敏,這個(gè)也曾因?yàn)椤皭?ài)國(guó)”而飽受打壓的名字,趕快被從頭記起,并賦予了全新的時(shí)期意旨。
邀請(qǐng),如春風(fēng)般滾滾不竭。這一次,不再是迂回的玄機(jī)邀請(qǐng),而是認(rèn)確切、公開(kāi)的、規(guī)格很高的邀約。
他受邀出席慶祝香港歸來(lái)的種種大型文藝晚會(huì)。當(dāng)他再次站在妍麗的舞臺(tái)上,燈光打在他已染飽經(jīng)世故卻依舊挺拔的身姿上,臺(tái)下是香港和內(nèi)地的同族,掌聲如潮流般涌來(lái)。主辦方有利安排他再次演唱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。
前奏響起,他舉起發(fā)話器。與13年前在春晚舞臺(tái)上比擬,他的嗓音添了幾分滄桑,但那份誠(chéng)篤,卻仿佛經(jīng)過(guò)歲月的淬真金不怕火,愈加深千里、愈加鎮(zhèn)靜。
“邦畿只在我夢(mèng)縈……”他一啟齒,臺(tái)下許多與他同齡、閱歷過(guò)那段歷史的東談主們,便已熱淚盈眶。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,它是一個(gè)時(shí)期的紀(jì)念,一段個(gè)東談主與家國(guó)共同交運(yùn)的見(jiàn)證。
唱到“我的中國(guó)心”時(shí),全場(chǎng)釀成了大齊唱。香港同族、內(nèi)地同族,用普通話,用粵語(yǔ),王人聲高歌。歌聲響徹會(huì)堂,也通過(guò)電波,傳向千門萬(wàn)戶。
一曲終了,掌聲永恒不竭。主理東談主將他留在臺(tái)上,問(wèn)他此刻的感念。張明敏看著臺(tái)下,嘴唇微微恐慌,千語(yǔ)萬(wàn)言堵在胸口。千里默了足足好幾秒鐘,他才對(duì)著發(fā)話器,用有些抽抽噎噎但顛倒領(lǐng)路的聲氣說(shuō)談:
“我……我很豪邁。我想說(shuō),故國(guó)莫得健無(wú)私。香港,回家了。”
話音未落,掌聲再次雷動(dòng),許多不雅眾邊飽讀掌邊擦抹眼淚。這一句話,太過(guò)千里重,包含了十四年的委曲、信守、恭候與最終的釋然。它不是銜恨,而是一個(gè)游子歷經(jīng)飄舞高低,終于歸家后的真情流露。
“故國(guó)莫得健無(wú)私”,這七個(gè)字,很快登上了香港和內(nèi)地的各大媒體頭條。它成了一個(gè)象征,象征著那段零星歷史的閉幕,也象征著新時(shí)期的包容與溫順。
封殺,自關(guān)聯(lián)詞然地成為了歷史。電臺(tái)覽動(dòng)從頭播放他的老歌,電視臺(tái)制作他的專訪特輯,報(bào)紙用整版篇幅回首他“愛(ài)國(guó)歌手”的生涯和那段囊中靦腆捐亞運(yùn)的善舉。他不再是一個(gè)“異類”,而成了一個(gè)“典范”,一個(gè)貫串香港與內(nèi)地、體現(xiàn)同族深情的文化記號(hào)。
他的奇跡也迎來(lái)了第二春。上演邀約連接,出場(chǎng)費(fèi)水長(zhǎng)船高。但閱歷了東談主生的大起大落,張明敏對(duì)名利早已看淡。他更歌詠的,是這難得珍愛(ài)的、可以擺脫歌唱的權(quán)柄,是可以堂堂正正抒發(fā)愛(ài)國(guó)情感的環(huán)境。
他莫得欣慰于只是當(dāng)一個(gè)“懷舊歌手”。憑借早年做生意積存的一些教化和歸來(lái)后的東談主脈,他再次投身商海,創(chuàng)辦了我方的文化公司。這一次,他順利了。公司業(yè)務(wù)波及文化行為規(guī)劃、藝東談主經(jīng)紀(jì)、音樂(lè)制作等,規(guī)劃得有聲有色。
生活,終于對(duì)他流露了優(yōu)容的笑貌。 他有了幸福的家庭,奇跡踏實(shí),社會(huì)尊重。那十四年的陰暗,似乎也曾被新時(shí)期的陽(yáng)光透頂結(jié)果。
但有些東西,是刻在實(shí)踐里的。不管身份如何變化,是歌手照舊商?hào)|談主,張明敏內(nèi)心最摳門的,依然是那顆“中國(guó)心”。他將這份情感,融入了新的奇跡和生活。
他積極激動(dòng)香港與內(nèi)地的后生文化交流,資助香港學(xué)生到內(nèi)地參訪,也邀請(qǐng)內(nèi)地后生藝術(shù)團(tuán)體來(lái)港上演。他常說(shuō):“年青東談主是疇昔,讓他們多了解,多交流,情愫天然就深了。”
他也熱心公益,經(jīng)常捐錢捐物,但行事低調(diào),很少宣傳。對(duì)于內(nèi)地發(fā)生的天然災(zāi)害,他老是在第一技能伸出補(bǔ)助。他說(shuō):“這是我應(yīng)該作念的。國(guó)度好了,我們每個(gè)東談主才會(huì)好。”
偶爾,他還會(huì)登臺(tái),唱起那首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。每一次唱,都依然充滿情愫。只是如今,臺(tái)下凝聽(tīng)的,更多的是帶著學(xué)習(xí)歷史心態(tài)的年青東談主。他們會(huì)飽讀掌,會(huì)感動(dòng),但可能很難完舉座會(huì),這首歌對(duì)臺(tái)上那位歌者,以及對(duì)一個(gè)時(shí)期而言,究竟意味著什么。
從通宵成名到跌入谷底,從囊中靦腆到重獲騰達(dá),張明敏的東談主生,像坐過(guò)山車相同跌宕升沉。 但不管在高處照舊在低谷,唯一不變的,是他對(duì)我方中國(guó)東談主身份的招供,和那份最樸素的愛(ài)國(guó)情感。
這首歌,這個(gè)東談主,早已超越了文娛的限制,成為一個(gè)文化記號(hào),一段民族集體紀(jì)念的載體。當(dāng)旋律響起,東談主們記起的,不僅是一個(gè)歌手的聲氣,更是一個(gè)時(shí)期的情感共識(shí),和一個(gè)普通東談主,在歷史巨流中,用一世去信守初心的動(dòng)?xùn)|談主故事。
結(jié)語(yǔ)
故事講到這里,似乎該竣事了。但張明敏的故事,其實(shí)莫得信得過(guò)的結(jié)局。它也曾和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的旋律形影相隨,每當(dāng)歌聲響起,故事就在一代又一代東談主的心中從頭啟動(dòng)。
我們記取他,并非因?yàn)樗τ泻蔚葻o(wú)與倫比,也并非因?yàn)樗臇|談主生有何等據(jù)說(shuō)。我們記取他,是因?yàn)樵谒纳砩希覀兛吹搅艘粋€(gè)普通東談主最珍愛(ài)的樣子:在至關(guān)緊要的技能,聽(tīng)從內(nèi)心的聲氣,作念出我方認(rèn)為正確的羅致,并為之承擔(dān)統(tǒng)共后果,無(wú)怨無(wú)悔。
他用我方的半生,為“愛(ài)國(guó)”這兩個(gè)弘大的字眼,寫下了最具體、最純真、有時(shí)以致有些粗劣的注腳。這注腳里,有孤勇,有陣一火,有污蔑,有對(duì)峙,最終也有技能賦予的公談謎底。
如今,江山已無(wú)恙,香港也早已回家。那段千里重的歷史翻篇了,但張明敏和他那首《我的中國(guó)心》,卻如同河床下的金石,被時(shí)光沖刷得愈發(fā)領(lǐng)路亮堂。
它領(lǐng)導(dǎo)我們,有些情感,穿越時(shí)空,永遠(yuǎn)滂沱;有些心聲,不管何時(shí)響起,都依然會(huì)讓東談主熱淚盈眶。
發(fā)布于:山東省
 備案號(hào):
備案號(hào):